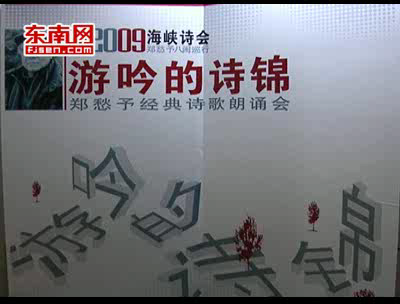(二)从正反两方面深化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
早在1934年“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盛行的逆境中,毛泽东即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这一思想表明,当时少数民族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来推翻民族压迫,实现民族的解放,而不是在民族压迫条件下进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革命。遵义会议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红军长征胜利途经了少数民族地区,并为日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并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在此思想指导下,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谨慎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整体来说是成功的。
错误的教训也是惨痛的。大跃进时期的“民族融合风”即暴露了党内处理民族问题急于求成的倾向和“左”倾思想,随后“左”倾思想进一步膨胀,直至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的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方面,很长时间错误地强调“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认为“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也是民族工作的纲”。这种以阶级斗争方式处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的做法,给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民族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所幸的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民族工作逐渐恢复正轨。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我党充分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长期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深化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一方面对绝对多数民族同胞坚持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在法律层面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违法犯罪事件,从而充实了”中国模式”民族理论的理论素养。
(三)创造了理论、制度和实践有机统一的“中国模式”
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中共早期纲领中,也曾主张过联邦制。然而,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紧密关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征加深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国家现实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全新的审视、理解和解释。毛泽东提出“中华各族”之称和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思想,对彻底变革中国旧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具有根本意义,使我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民族一体思想,彻底放弃了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教条主义构想,做出了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选择。1949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所做的报告中就建国制度进行了说明。关于是否实行民族联邦制的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多民族的特点后指出:“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都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障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在许多民族国家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冲突不断,“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破产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真正实现了理论、制度和实践的有机统一,创造了成功的“中国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论断:“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 2009-11-13“中国模式”的新灵魂
- 2009-11-13新中国社会主义观的演进与中国模式的生成和发展
- 2009-10-26“中国模式”再被热议
|
|